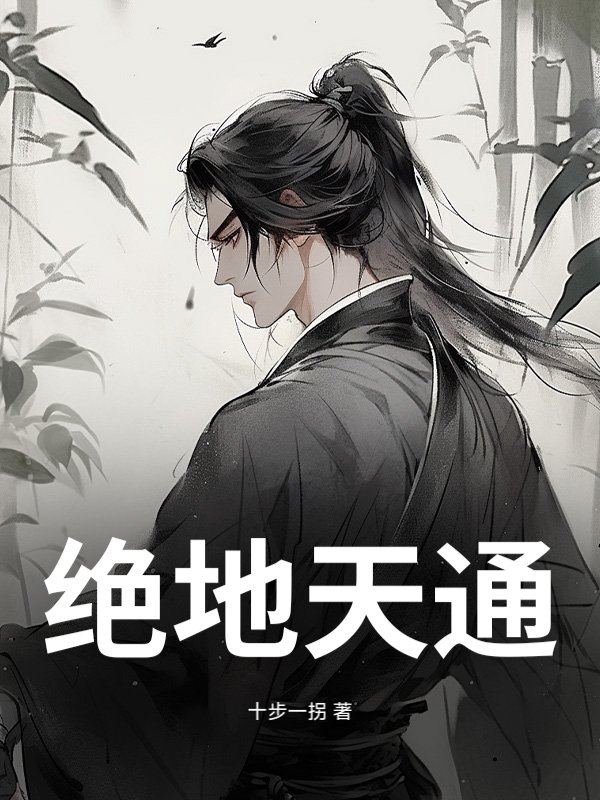苏焕心头一震,登时觉得‘有门’,反应快如闪电!他双手立刻在身前交错翻飞,如同穿花蝴蝶,瞬间结出“清心引”的后续三个变化印诀,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同时微微躬身回礼,姿态恭敬而不失本门风骨。
“哦?”青冥道人眼中讶色更浓,随即化为一丝了然的笑意。他放下手,目光落在苏焕身上,带着几分考校的意味:“钟真人的高足?难怪气度不凡。大丘山的‘清心引’三叠浪,可不是谁都能使得这般圆融。”
苏焕见对方识得大丘山秘传手印,心中更定,面上谦逊道:“道长谬赞,晚辈只是略通皮毛,不敢当‘圆融’二字。”
青冥道人微微颔首,似乎对苏焕的应对颇为满意。他沉吟片刻,又问道:“钟真人近年来可好?他那身功夫,想必已臻化境了吧?”
苏焕对其打探意味心中了然,从容答道:“家师安好,现在四处云游,参悟天地。家师曾言,此道浩瀚,他亦不过窥得门径,尚在砥砺之中。”这番回答既点明了钟元易的近况,又巧妙地避开了具体修为的探问。
青冥道人闻言,与旁边的玄苦和尚交换了一个眼神。玄苦和尚那古井无波的脸上,也微微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认同之色。
苏焕见这一僧一道颇吃这一套,心下稍定,便又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牌。这玉牌质地温润,刻工精良,正是钟元易座下嫡传弟子专属的信物。
那二人仔细查验,见玉牌不似伪作,再联想到方才苏焕所结的几个法印,不仅手法纯熟,更是大丘山一脉秘传的正宗路数,绝非外人所能模仿。这两样凭证一做身份说明,一做传承印证,和度牒比起来更加难以作假,青冥道人与那僧徒相视一眼,神色顿时缓和不少
青冥道人这才彻底放下疑虑,脸上露出一丝真切的笑意,对苏焕道:“原来如此。贫道青冥,早年曾与大丘山‘都讲’陈玄明道长和钟元易道长有过数面之缘,相谈甚欢。大丘山弟子向来清修自持,云游天下亦多不问世事,颇有出尘之姿,鲜少涉足这等红尘喧嚣之地。想不到今日竟能在此得遇钟真人的高徒,倒是意外之喜。”
苏焕连忙再次行礼:“原来是同和仙山的青冥前辈,失敬失敬。晚辈与师弟奉师门以及陈师伯之命下山云游,一来增长见闻,二来也是为宗门采买些山外之物。途径宝刹,仰慕法会盛况,更见此地霞光普照,气象万千,便想借贵寺宝地挂单几日,一来瞻仰盛景,二来也稍作休整。”他语气诚恳,将借宿的目的说得既含蓄又合情合理。
青冥道人当然听出了苏焕话中意味,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一旁的监院长老,脸上露出笑容:“智渊师兄,你看……这二位师侄既是大丘山钟真人的嫡传弟子,身份确凿无疑。其与我应身禅寺同处一州,也算是一脉同源的近邻了。他们想在寺中挂单几日,瞻仰法会,也算是一桩善缘。我寺向来大开方便之门,能否……安排一处禅房,容他们住下?”
监院长老细细的打量了一番二人,眼神中多了几分正色,随后缓缓的点了点头。应身寺寮元此刻见青冥道人亲自开口,监院长老也微微颔首,哪里还敢怠慢?连忙躬身应道:“青冥道长放心!我定会寻间清幽雅致的禅房供二位道长清修!慧明,还不快引二位道长过去?”
“是!”小沙弥连忙应声,看向苏焕和慕行舟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。
青冥道人满意地点点头,对苏焕二人和蔼地道:“二位师侄安心住下。老道与大丘山的‘都讲’陈玄明道长乃是至交,说起来也不算外人。若有闲暇,可来老道暂居的‘静观’坐坐,叙叙话。”
苏焕再次稽首:“多谢青冥师伯照拂,晚辈感激不尽。”他刻意用了“师伯”这个亲近的称呼。慕行舟也跟着行礼。
监院长老也合十道:“既是青冥道友作保,又是大丘山高足,敝寺自当以礼相待。二位道长请便。”他虽然语气依旧平淡,但那份拒人千里的疏离感已消散大半。
玄苦和尚身披简朴袈裟,手持一串盘得油亮的菩提子,脸上挂着平和的笑意。他微微颔首,双手合十,声音温润:
“阿弥陀佛。诸位所言甚是。无论是佛门禅院,抑或是道门洞天,出家人追寻本真、渡己渡人之心本无二致。天下寺观本就是一家,在这纷扰之世,能在应身禅寺的廊中与大丘山结下一段善缘,实乃一桩美事。善哉,善哉。”
监院智渊长老不再多言,对身后的玄苦大师和青冥子微微颔首:“二位,请随我来。”便带着两人,缓步向寺内深处走去。那位寮元老僧立刻从云水堂内小步快跑出来,躬身在前引路。
山门前,香客如织,摩肩接踵。鼎沸的人声、袅袅的香烟、此起彼伏的诵经声交织成一片喧嚣的洪流,几乎要将那巍峨的山门淹没。
苏焕、慕行舟与周澹台三人,也紧随其后。一众人等跟着为首带路的寮元,绕过门内门外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的信众香客,并未走向正殿方向,而是拐入一条僻静的回廊,从一处不起眼的小侧门进了寺内。
穿过小门,仿佛瞬间踏入另一个世界。身后的喧嚣如同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绝,骤然减弱,只剩下模糊的声音音。眼前是一条向上延伸、被高大院墙夹峙的青石小径,光线骤然昏暗,空气中弥漫着古寺特有的、混合着苔藓藓、香灰和旧木的沉静气息。
门内门外仿佛是兩個世界。寺外喧嚣鼎沸,寺内却别有洞天,且规模宏大。整个寺庙依山势而建,盖在半山腰上,地势忽高忽低,回廊、台阶、院落层层叠叠,错综复杂。沿途所见,有些院墙平整光滑还刷了红漆,显得庄重气派,显然是重要殿宇或僧寮所在;有些地方却只是由整整齐齐的石头垒成,古朴粗犷,透着岁月的痕迹。路径迂回曲折,若非有人带领,初次至此非得迷路不可。
在一个三岔路口,寮元停下脚步,对身后众人略一颔首,便领着大部分访客转向了右侧一条通往客堂方向的回廊。而一个早已等候在旁、约莫十二三岁、眉清目秀的小沙弥——慧明,则双手合十,对着苏焕、慕行舟和周澹台微微躬身,声音清脆而平静:“三位施主,请随小僧来。”他的目光在周澹台腰间那枚形制古朴的木牌上短暂停留了一下,随即转身,引着三人走上了左侧一条更为幽静、似乎通往更高处的石阶小径。
小径尽头,一处僻静的院落出现在眼前。院墙是未经粉刷的粗石垒成,爬满了藤蔓,院门虚掩。推开院门,里面是一方不大的天井,一棵苍劲的古松遮蔽了小半天空,树下石桌石凳,清幽异常。正对着是三间相连的禅房,门窗皆是原木色,窗纸素白。
慧明引着三人进入中间那间禅房。屋内陈设极其简单:通铺、矮柜、方桌、木椅、油灯、陶壶陶碗,一尘不染,却透着一种近乎刻板的清寒。慧明待三人站定,从宽大的僧袖中取出两枚小巧的木牌,色泽温润,形制、纹理与周澹台腰间悬挂的那枚别无二致,分别递到苏焕和慕行舟手中。
“此乃寺内腰牌,请二位施主随身佩好。”慧明的声音依旧平静无波,“凭此牌,可在寺内行走,斋堂用饭。斋堂在东北角‘五观堂’,每日卯时、午时、酉时三刻开斋,过时不候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三人,“若有其他需用,可寻院中或附近过路的师兄指引。小僧告退。”
说罢,慧明双手合十,对着三人微微一躬,便转身走出禅房,步履轻悄无声,如同融入院落的暮色之中,很快消失在院门外曲折的小径尽头。禅院内,只剩下苏焕、慕行舟和周澹台三人,以及手中那枚带着古寺木香的寺客腰牌。远处,隐约传来悠扬的暮鼓声,更衬得这小院寂静非常。
慕行舟等慧明走后,仔细的环视一周,轻轻“啧”了一声:“这应身禅寺,倒真是‘应身’得很。外面看着大气磅礴,里面给客人住的地方,倒比苦行僧的茅棚也强不了多少。”他拍了拍硬邦邦的床铺,“这褥子,怕是还没马鞍软和。”
周澹台的声音在清冷的禅房里响起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调侃和无奈:“知足吧,赵兄。这地方所需之物应有尽有,景致也还过得去。你是没瞧见西边塔林那一片——信众们捐的几十座宝塔,如今大半都腾出来塞人了!那地方,啧啧……”他摇摇头,脸上露出一副不堪回首的表情,“好些塔里,鸟粪都没扫干净!山风一起,拍得那破窗棂‘哐当哐当’响,保管你半夜三更被那动静惊醒,疑心是哪个圆寂的老和尚回来敲门了。”
他话锋一转,目光在慕行舟和苏焕身上溜了一圈,带着几分打趣,又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探究:“啧啧,想不到二位道兄竟是大丘山的高足!到底是名门正派出来的,这待遇果然不一样!瞧瞧这禅院,清幽雅致,窗明几净,比那闹鬼的塔林子强了不知多少倍!”
慕行舟闻言,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,肩膀随意地耸了耸,语气带着点自嘲又带着点不以为意:“得了吧,周兄。名门高足?还不是差点让个看门的和尚拦在山门外头喝西北风?要不是靠着点长辈的交情,脸皮够厚,磨破了嘴皮子,这会儿咱哥俩指不定在哪片野地里蹲着呢!这禅房,算是沾了祖师爷的光,捡了个漏。”
周澹台嘿嘿一笑,拍了拍慕行舟的肩膀:“话不能这么说!能在寺里弄到这么一间房,甭管靠的是祖师爷的面子还是自己磨来的,那就是本事!这年头,能在这应身禅寺里占个安稳窝的,都不是简单人物。”
苏焕没有接话,则是径直走到窗边。那扇糊着素白棉纸的木窗,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单薄。他伸出手,指尖触到窗棂,轻轻一推。
“吱呀——”
木轴转动,发出一声干涩的轻响。一股带着山林特有清冽和香烛余韵的晚风,瞬间涌入室内,吹散了方才的沉闷。
窗外,并非一览无余的开阔。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几座与脚下这间禅院形制相仿的楼阁,灰瓦白墙,飞檐翘角,它们彼此间隔不远,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片山坡上。
而更远处,越过这些相邻的楼阁屋顶,视野才豁然开朗。只见层层叠叠、依山势而建的宏伟殿宇,如同一条沉睡的巨龙,盘踞在起伏的山峦之上。琉璃瓦顶在最后一抹天光的映照下,反射出幽暗的金色光泽;巨大的斗拱层层叠叠,支撑着深远的屋檐;飞檐如同巨鸟展翅,直刺向灰蓝色的天穹。殿宇之间,有回廊相连,有高塔耸立,更有无数小如蚁穴的僧舍、经堂点缀其间,构成一幅宏大而森严的画卷。
晚钟的余韵似乎还在山谷间回荡,更衬得这片建筑群庄严肃穆。